泉州非遗景点洛阳桥,重游一次走进蔡襄,走近《康定情歌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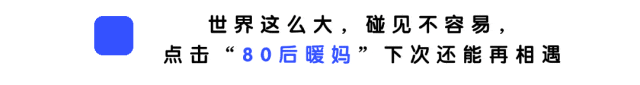

这名字一开始听着,心里总想着:是那个古诗词中的洛阳吗?
但它其实一直就在泉州,在洛阳江入海口那一片很淡很淡的黄昏里。
洛阳桥很长,一眼望不到头,桥面是一块一块青石板铺成的,每一块都像一段被人磨了很多年的心事,沉默、平整,偶尔有自行车碾过去,轮子和石缝轻微地磕碰了一下,又很快消失在风里。
洛阳桥本名不叫洛阳桥,叫万安桥。
万安渡,听名字就知道,从前人想得很简单——只求万世安澜。
渡口太凶,船翻了,人沉了,最后是蔡襄站出来,主持修了这座桥。
六年的时间,一块一块石头,一船一船地运,在江水最急的地方,用“筏形基础”,再在石头上养牡蛎,让它们一层一层地裹住桥墩,像时间裹住人一样,把桥牢牢钉在水里。这就是“种蛎固基”,说起来轻巧,做起来,是要搭上许多人命、汗水和等待的。
我站在桥中间,往下看,水一半是江,一半是海,颜色混在一起,分不清哪一半更咸一些。
桥墩上有石将军,站在那里快一千年,腰杆还挺得笔直,但脸已经被海风磨得看不清五官。
我猜他们心里一定有一句话,很想说出来,可站得太久,已经忘记了第一声该说什么。
村口有一条老街,叫做洛阳街,名字听着气派,其实不过是一条石板路,两边是红砖厝和旧式骑楼,墙皮剥落了一些,露出里面深红色的砖。
巷子里有老人搬着小椅子在门口坐,有人扇着蒲扇,有人低头剥花生,他们看我像看一个走错门的人,又像早已看惯了我这样的外来者。

昭惠庙在桥北的万安村里。
昭惠庙很旧,但很干净。门口有几块碑,字都有些模糊,凑上去才勉强读出来,原来这是为修洛阳桥建的庙,是“指挥部”,也是精神支柱。
当年蔡襄修桥,信不过自己,也不完全信石头,就从九日山请来海神通远王,把庙建在江边,一边指挥工程,一边祈求风平浪静。
庙里面很安静,香火一点一点地烧,烟气细得像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。
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,里面有人跪拜,背影很弯,不知道是在求海,还是在求一段不太顺利的日子。
庙里有一方清代的石匾,“昭惠庙”三个字写得端正,是后来的人题上去的,但那种小心翼翼、怕得罪谁又怕谁看不见的心情,还是从石头里渗了出来。
从昭惠庙出来,没走多远,就是吴文秀故居。

其实应该叫吴文季故居。
那个把《康定情歌》带出大山、带出康定、带出中国,最后让它变成很多人课本里一段旋律的人,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
故居不大,甚至可以说是小。一个院门,一条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巷子,再推开门,就是一个小小的天井,几间屋子。墙上挂着他的照片和生平介绍,还有那首《康定情歌》的谱子。
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,心里有一点点难过,但又不完全是难过。他一生坎坷,很多年都在压抑和不被理解里度过,可墙上的那句话,写得很淡——“他一生坎坷,却终生为自由而歌。”
这句话像是一句总结,也像是一句他自己才听得懂的笑话:命运把你摁进泥里,你偏要从泥里唱出声来。
可惜门没开,只能顺着旁边的巷子,靠着窗户望进去看看

蔡襄站在桥头很高的一座塑像上,手好像伸在指路,又好像只是伸出来,接一接风。
他不是这里的人,却成了这座桥最离不开的人。他是状元,是书法家,是“宋四家”之一,字写得端庄、温和,像一条不太容易生气的河。
可他修起桥来,一点儿都不温柔——石块巨大,十几吨一条,一块一块架上去,架了六七年,架出了一座“中国古代桥梁的状元”。
桥南有蔡襄祠,里面有《万安桥记》碑,短短一百多个字,把时间、银子、人名、用处都写得很清楚。书法、文章、雕刻,后来的人说这是“三绝”。
我站在碑前,只觉得一个字:克制。
一个在权力和人心之间走了一辈子的人,写起字来也克制,讲起话来也克制,连“我很不容易”这几个字,都藏在纸的背后,不肯直接说出口。
我想,蔡襄当年一定也有过很多夜晚睡不着的时候。
江水太急,风向不定,钱不够用,人手也不够,庙里的香火烧得旺不旺,桥墩上的牡蛎长不长得牢——这些他一定都反复想过。
可他站在塑像上,只留给我们一个安静的背影。不喊冤,不邀功,好像做这一切都只是因为“应该做”。
从桥上望出去,洛阳江两岸是大片大片的红树林。

“红树林”这个名字起得有点骗人,远看是一片深绿,走近了才发现,树干是红的,树根像无数只细瘦的手指,抓紧了淤泥,从水里挣扎着站起来。
这里是福建乃至全国现存面积最大的连片人工红树林之一,说是“海岸卫士”,因为它替人挡住了风浪,替人守住了泥沙,也替许多生命留了一片可以落脚的地方。
红树林里全是鸟。
白鹭最多,像一筷子插在水里的白色筷子,又像一群不太会算时间的人,总是落在最不应该落的地方。
牛背鹭站在牛背上,池鹭蹲在水边,一动不动,像是等待一个不会来的人。
退潮的时候,滩涂露出来,鸻鹬类在泥上跑来跑去,脚步很急,像赶着去赶一场早已经散场的集市;涨潮的时候,水面抬高,它们就站到红树林里,树叶子把风挡了一半,鸟叫传到人耳朵里,也只剩下一半。
有几只鸟从我头顶飞过去,翅膀扇得很用力,影子落在红树林上,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。我忽然觉得,人和鸟的差别,其实不大。
鸟在红树林里找食,人在世界里找意义;鸟退潮了去泥滩,人遇事了去庙里、去桥头,去找一个能托付心事的地方。
红树林的外围,还有滩涂,有小螃蟹横着爬,有弹涂鱼跳来跳去,像一群不太懂事的孩子。
远处有一艘小船搁在泥上,船底发白,像是被人忘记的一句话。
天彻底暗下来的时候,我站在洛阳桥中间。
左边是桥北的万安村,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,昭惠庙的飞檐在暮色里显出一条淡淡的轮廓;右边是桥南的蔡襄祠和红树林,红树影影绰绰,被风吹得轻轻晃动。
风从江面上吹过来,吹到脸上有点湿,也有点凉。
我忽然想起蔡襄、想起那位把《康定情歌》从山里带到世界的人、想起海神通远王、想起庙里那些跪拜的背影、还有那些在红树林里飞来飞去的鸟——他们之间,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,很细,却一直连着。
有人为了一座桥花去半辈子,有人为一首歌耗尽一生,有人为了一艘船的平安跪在庙门口,也有人什么都不求,只是在红树林里飞一圈,落下来,歇一会儿,又飞起来。
时间过去,石头旧了,庙翻修了几次,故居里多了几张照片,红树林一年一年地长,鸟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。
人能留下的东西,其实不多。

写在最后
天慢慢暗下来,我没有急着走,而是靠在栏杆上,看那江水一点点把倒影吞没。
我忽然明白,其实人和桥的相遇,也就是人和命运的一次照面。
蔡襄当年修这座桥,是为了让人过得去;我们现在走这座桥,往往是为了走回来。昭惠庙里的香火,吴文季故居里的歌声,还有红树林里那些永远不安分的鸟
说到底,都是在讲同一件事:人这一辈子,就是在泥里挣扎着想要站直,在风浪里拼命想找一块落脚的石头。
洛阳桥站了一千年,它看惯了热闹,也看惯了冷清。
它不说话,是因为它知道,所有的喧嚣最后都会像潮水一样退去,留下的,只有那些沉默的石头,和石头里一层层长出来的硬壳。
我们这些从桥上走过的人,不过是像那些鸟一样,扑棱着翅膀,停一下,叫几声,以为自己留下了什么,其实对桥来说,连一阵风都算不上。
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
生活本来就没有意义,非要在这种无意义里,硬生生地凿出一个窟窿,透进一点光来,这或许就是我们还得接着走下去的理由。
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尊蔡襄的塑像,他在夜色里成了一个剪影,像极了一个没走完路、却先坐下来歇脚的赶路人。
风吹过,他没动,桥也没动,只有我的心,好像被轻轻碰了一下,然后跟着风,慢慢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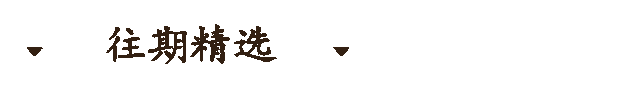
相关文章
发表评论
评论列表
- 这篇文章还没有收到评论,赶紧来抢沙发吧~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