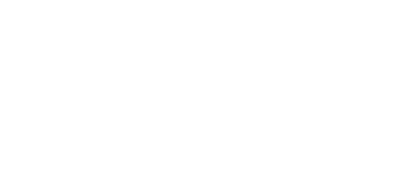别不信,没有500万字景点阅读垫底,所谓的“思辨性阅读”只是贴标签喊口号
读《中庸》,有句话一直忘不掉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”从前只把它当学习步骤记,这些年才慢慢咂摸出味道——博学被放在最前头,不是偶然的。 没有“博学”这个“一”,后面那些“审”“慎”“明”“笃”全是空中楼阁。
思辨性阅读,说到底是个厚积薄发的事。古人从不把“思”与“学”拆开,《论语》开篇就说“学而时习之”,孔子讲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,两句话像榫卯,扣死了读与思的关系。
学是吸纳,思是消化。不学而思,好比空锅煮水,火再旺也烧不开;而不思之学,又像往漏筐里倒米,装多少洒多少。这套道理朴拙得很,却常被今日谈论思辨的人忽略。他们爱讲批判、爱讲质疑、爱讲独立思考,仿佛只要掌握了几种思维技术,人就能凭空智慧起来。可古人比我们诚实:没有万卷书垫底,你拿什么去思、去辨?
苏轼写过一篇《日喻》,讲一个生来失明的人问太阳什么样。别人告诉他“日之状如铜盘”,他敲铜盘,听见钟声,以为那是太阳;又有人告诉他“日之光如烛”,他摸蜡烛,摸到籥这种乐器,以为那就是太阳。这故事我每读一次,后背就凉一次。今天许多所谓“思辨”,不正是这种“扣盘扪籥”么?
读了几篇时评,刷了几段短视频,便敢对流传千年的经典指指点点。好像思辨就是换个角度挑毛病,谁的立场更新奇,谁就更“有思想”。殊不知,真正的质疑远比这难——你得先钻进古人的脑子,替他把道理从头到尾捋一遍,看清楚他是在什么处境下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、调动了哪些资源,才配得上说一句“我以为不然”。没有这个“钻进去”的功夫,所谓的“批判”,不过是另一种盲从。
杜甫说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。从前只当是谈写作,后来才懂,那个“破”字是功夫眼。书不读到“破”的程度,里面的筋骨是看不见的。我读《史记》,头一遍只看见故事,第二遍看见人物,第三遍看见司马迁藏在字缝里的泪与笑——看见他写项羽本纪时笔端的悲慨,写货殖列传时眼里的冷峻。这些层层叠叠的理解,没有三四遍、五六遍是生不出来的。而每一遍新读,都是与前一遍的自己思辨:你推翻昨日的理解,修正上周的判断,像堆柴火,一层压一层,最后才烧得起那一把火。
有人担心:书读多了会不会把自己读成“两脚书橱”?宋儒早回答过这个问题。程颐说:“学原于思。”读进去的东西,若不经过思的蒸腾,确实只是死知识。可反过来,不读够本钱,思什么呢?程朱一辈子注经,不是匍匐在圣人脚下。他们是真读透了,才敢在“格物”二字上与古人辩一辩。朱子改《大学》,“在新民”还是“在亲民”的取舍,背后是多少日夜的字斟句酌。没有那几十年的功底,他改一个字都站不住脚。
郑板桥有副对联,被人用得滥了: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。”少有人细想:三秋树的“简”,是从夏之繁、春之萌一步步走过来的;二月花的“新”,是熬过了一整个冬的萧索。思辨的“新”也是如此——它不是凭空开出的花,是从千万卷书的老根里,慢慢顶出来的那一星嫩芽。
今天常听人问:读经典有什么用?又不能直接变现。这问题本身,就是读得太少的症候。必读经典的分量,不在那些可以被检索的“知识点”,而在它们搭建的那套认知坐标系。有了这个坐标系,随便翻开一本新书,你都能迅速定位:这是前人谈过的老问题,这是当下才有的新命题,这是对旧说的继承,那是对传统的反动。没有这个坐标系,读再多也像没头苍蝇,转不出信息的迷宫。
思辨从来不是无根的挑剔,而是有根的对话。根扎得越深,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,才越能辩出些真东西来。有500万字经典阅读的垫底,所谓的“思辨性阅读”只是贴标签喊口号而已。
相关文章
发表评论
评论列表
- 这篇文章还没有收到评论,赶紧来抢沙发吧~